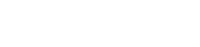信的日期很杂,有去年二月份的,也有上礼拜刚寄出的,写到激动处,字母连成一长串儿鬼画符,沉知墨费了些心力才看懂,好不容易翻译完一页,底下还有厚厚一大沓。
天黑之前能翻完吗?
她用手捏住酸痛的后颈,仰起脑袋活动了几下。
姓季的丧尽天良,不仅给孕妇上手铐,还让孕妇如此费心劳神。
沉知墨暗骂了几句,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爬床翻窗的“英勇”行径。
这一休息,恰巧瞧见一只布鞋从门槛踏了进来。
来人一身长衣长裤,衬衫扣到了最上面颗,紧箍着脖子,勒得脸蛋深了几个色,手上端碗绿豆汤,看见她看自己,少女三步并作两步疾走到桌旁,碗底敲到桌面,闷一声“咚”,末了马上又要走,沉知墨抓住那只腕子,
“穿这么厚,小心捂出痱子来。”
方语无言,只是转动手腕。
“我去租界找过你。”
手心的转动停了,沉知墨将方语拉近一步,
“到处找不到你……原来是你不听话,要来当土匪,姓季的给你什么好处了?你这么舍不得她?你知道她杀了多少人?爸……谢晋现在还瘫着,这女人蛇蝎心肠,你跟着她有命赚钱也没命花!”
方语眸光颤颤,对上沉知墨的视线。
方才隔门窥见的那位婷婷淑女不见了,沉知墨不动不说话的时候,总有股清冷出尘的书卷气,她心一软,知道她上火就给煮了绿豆汤送来,忘了自己一开始就是被这副样子给骗惨了。
这才是真正的沉知墨,自私的、自大的、用金钱衡量一切的沉知墨,她无比后悔昨夜同沉知墨发生了关系。
因为她只能射出来精,射不出人性净化剂。
方语另只手掰开束着自己的手指,快步走到门口,又回头比划了一句:[她不是你说那样。]
“你……”
再想说什么,也只能望着背影说了,沉知墨烦闷地垂下头。
行,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,她已经放低身段了,方语还要怎么样?难不成要当座神像供起来才肯罢休?
或者一句诚恳的道歉,或者一句……我爱你。
不,她做不到。
爱不是投资,而是捐赠,爱向来是方语舍予她的东西,她不愿对调身份,也没有那么慷慨。
沉知墨重新投入进繁冗的翻译工作,这次速度快了很多,大概是没有坏想法来分心的缘故。
翻译并不只字转换成字那样简单,写的人用心声过一遍再落于纸上,已有歧义,翻译的人又用干巴教材上学来的过一遍,心声再过一遍,中间转了好几道,怎么译都不太对味。
这方面沉知墨又是个爱钻牛角尖的,等她字斟酌句地翻译完全部信件,天幕已缀满繁星点点,她伸了个懒腰,把翻译完的纸张通读一遍,却是越读越心惊。
刚刚忙着和单词做斗争,忽略了内容的前后关系,只记得什么苏西露易丝的,信大多是苏西写给露易丝的,这俩人名十个外国人里能挑出来八个,她并没有很留意,但一结合信的内容……
她隐隐想起,傅太太的夫人,傅部长,英文名便是苏西,而另一位……
沉知墨匆忙扶桌站起,起身快了,头有点晕,此时也顾不得了,季曼笙屋里的灯熄了,她急促地拍了几下房门,
“谁?”
见灯亮起,沉知墨径直推开房门进了屋,“这些信,你从哪儿来的?”
季曼笙从床上坐起来,打了个哈气,拉起右边肩膀的睡衣吊带,“译完了?”
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!”
“我自有门道。”说罢,季曼笙接过沉知墨手上的纸张,对着油灯翻了几页,“译得挺好。”
“你看得懂?为什么又叫我翻译?”那她费心费力忙活一通不就竹篮打水……
“别生气嘛,测试你乖不乖而已。”
“你!”
“好啦好啦。”季曼笙手臂一伸,将沉知墨拉坐到榻边,“表姐,你真的好香。”
“不要碰我!”红指甲描摹着下颌轮廓,激起沉知墨一身冷汗。
“好好,不开玩笑了,这不是为了拖表姐你下水嘛……”
床上的人权当听不见,自顾自将下巴放到沉知墨肩膀上,“有没有觉得我们更亲近了?”
“这是外交部长写给海关监督的信,对吗?”
现任外交部长傅英,预备把奉安一半的地界都租给法国人。
怪不得近些日子街上多出那么多洋面孔……名义为租……只怕租着租着,就变成了别人家的私产。
“就喜欢你那么聪明。”
“你想做什么?”
“你不是应该猜到了吗?”
红唇越靠越近,热腾腾的人气儿烘烤着耳畔,沉知墨闭起眼睛,用力把季曼笙推回床上,“你在找死!”
“你愿意帮我吗?”
“你明知道!而且我告诉你,你别想把小语拖下水,谢月枫葬礼完了我就带她走!”
“别忘了你还欠着我人情。”季曼笙无所谓地耸耸肩。
天大的人情,也不值当用命去还。
沉知墨尽力止住身躯的震颤,“你想要多少钱?”
“我不缺钱……你知道的,有命挣没命花。”
季曼笙又偷听她讲话!
“你不还这个人情,我有的是法子叫阿语留下来。”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又想让我干什么?”提到方语,沉知墨终是退让了一步。
“阻止汉奸卖国,必要时除掉她,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“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,是政府的决定,除掉傅英,也会有下一个傅英……”
“我不管。”
“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高尚?”
一个土匪,跟她谈什么爱国!
“我没有这样认为。”季曼笙往前坐了一点,牵住沉知墨的手,“这事儿谢老头也出了一份力,他想晋到副总统的位置……对,我不是好人,杀人放火我都做过,我也不能保证掌控奉安后我能不贪污、不腐败,但你要知道,这些事的前提都是国家还在,才有得贪,有得败,这群人已经丧心病狂了,你知道他们转移到国外的存款有多少吗?”
季曼笙比出两根指头,“光谢老头,就足足八千万。”
八千万……无论哪个货币单位,都是骇死人的数字。
“我不想管这些……我真的不想管……”沉知墨扬起头,抑住快要夺眶的热泪。
“小沉。”季曼笙从床上跪起来,替她擦掉了眼角的泪珠,“我以前跟你一样……不,我比你还要……我已经后悔过了,我不希望你后悔。”
天黑之前能翻完吗?
她用手捏住酸痛的后颈,仰起脑袋活动了几下。
姓季的丧尽天良,不仅给孕妇上手铐,还让孕妇如此费心劳神。
沉知墨暗骂了几句,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爬床翻窗的“英勇”行径。
这一休息,恰巧瞧见一只布鞋从门槛踏了进来。
来人一身长衣长裤,衬衫扣到了最上面颗,紧箍着脖子,勒得脸蛋深了几个色,手上端碗绿豆汤,看见她看自己,少女三步并作两步疾走到桌旁,碗底敲到桌面,闷一声“咚”,末了马上又要走,沉知墨抓住那只腕子,
“穿这么厚,小心捂出痱子来。”
方语无言,只是转动手腕。
“我去租界找过你。”
手心的转动停了,沉知墨将方语拉近一步,
“到处找不到你……原来是你不听话,要来当土匪,姓季的给你什么好处了?你这么舍不得她?你知道她杀了多少人?爸……谢晋现在还瘫着,这女人蛇蝎心肠,你跟着她有命赚钱也没命花!”
方语眸光颤颤,对上沉知墨的视线。
方才隔门窥见的那位婷婷淑女不见了,沉知墨不动不说话的时候,总有股清冷出尘的书卷气,她心一软,知道她上火就给煮了绿豆汤送来,忘了自己一开始就是被这副样子给骗惨了。
这才是真正的沉知墨,自私的、自大的、用金钱衡量一切的沉知墨,她无比后悔昨夜同沉知墨发生了关系。
因为她只能射出来精,射不出人性净化剂。
方语另只手掰开束着自己的手指,快步走到门口,又回头比划了一句:[她不是你说那样。]
“你……”
再想说什么,也只能望着背影说了,沉知墨烦闷地垂下头。
行,千错万错都是她的错,她已经放低身段了,方语还要怎么样?难不成要当座神像供起来才肯罢休?
或者一句诚恳的道歉,或者一句……我爱你。
不,她做不到。
爱不是投资,而是捐赠,爱向来是方语舍予她的东西,她不愿对调身份,也没有那么慷慨。
沉知墨重新投入进繁冗的翻译工作,这次速度快了很多,大概是没有坏想法来分心的缘故。
翻译并不只字转换成字那样简单,写的人用心声过一遍再落于纸上,已有歧义,翻译的人又用干巴教材上学来的过一遍,心声再过一遍,中间转了好几道,怎么译都不太对味。
这方面沉知墨又是个爱钻牛角尖的,等她字斟酌句地翻译完全部信件,天幕已缀满繁星点点,她伸了个懒腰,把翻译完的纸张通读一遍,却是越读越心惊。
刚刚忙着和单词做斗争,忽略了内容的前后关系,只记得什么苏西露易丝的,信大多是苏西写给露易丝的,这俩人名十个外国人里能挑出来八个,她并没有很留意,但一结合信的内容……
她隐隐想起,傅太太的夫人,傅部长,英文名便是苏西,而另一位……
沉知墨匆忙扶桌站起,起身快了,头有点晕,此时也顾不得了,季曼笙屋里的灯熄了,她急促地拍了几下房门,
“谁?”
见灯亮起,沉知墨径直推开房门进了屋,“这些信,你从哪儿来的?”
季曼笙从床上坐起来,打了个哈气,拉起右边肩膀的睡衣吊带,“译完了?”
“你先回答我的问题!”
“我自有门道。”说罢,季曼笙接过沉知墨手上的纸张,对着油灯翻了几页,“译得挺好。”
“你看得懂?为什么又叫我翻译?”那她费心费力忙活一通不就竹篮打水……
“别生气嘛,测试你乖不乖而已。”
“你!”
“好啦好啦。”季曼笙手臂一伸,将沉知墨拉坐到榻边,“表姐,你真的好香。”
“不要碰我!”红指甲描摹着下颌轮廓,激起沉知墨一身冷汗。
“好好,不开玩笑了,这不是为了拖表姐你下水嘛……”
床上的人权当听不见,自顾自将下巴放到沉知墨肩膀上,“有没有觉得我们更亲近了?”
“这是外交部长写给海关监督的信,对吗?”
现任外交部长傅英,预备把奉安一半的地界都租给法国人。
怪不得近些日子街上多出那么多洋面孔……名义为租……只怕租着租着,就变成了别人家的私产。
“就喜欢你那么聪明。”
“你想做什么?”
“你不是应该猜到了吗?”
红唇越靠越近,热腾腾的人气儿烘烤着耳畔,沉知墨闭起眼睛,用力把季曼笙推回床上,“你在找死!”
“你愿意帮我吗?”
“你明知道!而且我告诉你,你别想把小语拖下水,谢月枫葬礼完了我就带她走!”
“别忘了你还欠着我人情。”季曼笙无所谓地耸耸肩。
天大的人情,也不值当用命去还。
沉知墨尽力止住身躯的震颤,“你想要多少钱?”
“我不缺钱……你知道的,有命挣没命花。”
季曼笙又偷听她讲话!
“你不还这个人情,我有的是法子叫阿语留下来。”
“你到底想干什么?又想让我干什么?”提到方语,沉知墨终是退让了一步。
“阻止汉奸卖国,必要时除掉她,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”
“这不是她一个人的决定,是政府的决定,除掉傅英,也会有下一个傅英……”
“我不管。”
“你是不是以为自己很高尚?”
一个土匪,跟她谈什么爱国!
“我没有这样认为。”季曼笙往前坐了一点,牵住沉知墨的手,“这事儿谢老头也出了一份力,他想晋到副总统的位置……对,我不是好人,杀人放火我都做过,我也不能保证掌控奉安后我能不贪污、不腐败,但你要知道,这些事的前提都是国家还在,才有得贪,有得败,这群人已经丧心病狂了,你知道他们转移到国外的存款有多少吗?”
季曼笙比出两根指头,“光谢老头,就足足八千万。”
八千万……无论哪个货币单位,都是骇死人的数字。
“我不想管这些……我真的不想管……”沉知墨扬起头,抑住快要夺眶的热泪。
“小沉。”季曼笙从床上跪起来,替她擦掉了眼角的泪珠,“我以前跟你一样……不,我比你还要……我已经后悔过了,我不希望你后悔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