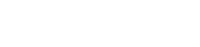美国西部 加尼福利亚州 内森铜矿场
狂风、暴雨、夜。
风卷着大雨扑面而来,一截细长的黑影躬着身子,进一步,退半步,踉跄地行走在铁路上。
手提电筒的光越来越近,晃晃映到雨幕里,为了躲避这只光的眼睛,黑影惊恐地趴到了地上,变为匍匐前进。
铁轨下的枕木散发出腐臭的气息,这里每根木头下面都埋葬着一位中国劳工的尸体,这是几十年前就经历过一次的教训,她怎么还会上当?
雨靴踩过碎石子,发出吱吱喳喳的声响,光落到手边,她停止了呼吸。
背心被雨靴踩出一个洞,靴底的碎石嵌进了肉里。
“找到你了,死猪仔。”
她先是感到疼痛,然后是愤怒,无止尽的愤怒,“你也是中国人!做这种事不怕遭报应吗!”
就是这个人,就是这个人……跟她说这里遍地都是机遇,面包多到拿来铺路,打开水龙头流的是牛奶,还慷慨地替她支付了60美元的船票。
即使睡在甲板底下经历了80天的颠簸,期间享受着和牲畜齐平的待遇,她也没有怀疑过这个人。
“报应?”衣领被提起,眼窝挨了一记重锤,一下、两下……她终于受不了了,滑下去抱住那只雨靴。
“求求你……求求你放了我……”
没有用。
那人揪住她的后衣领,将她往回拖,脚后跟踢踢踏踏击打着枕木,她几乎就要万念俱灰了。
是啊,求饶有用的话何必逃跑?
显然需要,更直观的好处。
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,还有谁能帮她?
一张脸闪过脑海,她惊叫起来,“我想起来了!我想起来了!”
“鬼叫唤什么?”
“你知道奉安的谢晋谢元帅吗?我有……”她捋捋乱抖的舌头,吞下一口雨水,“我有个姐姐,嫁给了谢元帅的女儿,只要你让我写封信!只要你让我写封信给她!她一定会帮我!你要多钱都行!”
雨靴在地面敲了几下,磕掉几颗石子,良久,头顶传来计算完毕的声音,“两千。”
“可以!可以!”
“信你一次,要收不到钱,你知道下场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树林一片片略过车窗,路边渐渐出现零星行人,挂着谢家的车牌,一路的小关卡畅通无阻,但城门那关……
方语将手伸出车窗,期望风能吹散紧张的汗水。
这是她第一次跟季曼笙出任务,今天的任务很简单。
送信。
如果她能干一些,压根用不着季曼笙顶着一张通缉令上的脸招摇过市,每次她想要帮她,季曼笙总会说,还不到时候,或者,你心太软,做不成事。
方语收回手,捏住膝盖,显出几分闷闷不乐之色。
“怎么?还在跟表姐闹别扭?”
摇头。
“表姐是毛病多了点,但有一点好……”
她向来很会断句,吊人胃口,方语忍不住偏了点脑袋,季曼笙借这机会瞟了一眼后视镜,接着说道:“就是自私。”
[自私有什么好?]
沉知墨的自私可害苦了她。
“我昨儿问表姐,如果鬼子拿枪逼她,让她交代事情,她会不会说,你猜怎么着?”
[她会。]
“对了,她会,在这年头是最聪明的选择,要死死一个,免得全家跟着遭殃。”
[我还是不懂。]
“那么你希望表姐在老家踏实跟你过日子吗?”
不……如果她渴求的是一位踏实敦厚的妻子,大可以在村里挑拣一位门当户对的,她喜欢沉知墨,一开始就是因为那一抹,不同。
追求新鲜事物是人的本能,她愿意供沉知墨念书,或许也是将自己对新世界的渴望投射到了沉知墨身上。
季曼笙换了只手握方向盘,朝窗外一抬下巴,“那就是不自私的人的下场。”
道路旁,几位身着长衫的学生被士兵推搡着前行,他们失去了昨日游行时的威风,面如枯槁,跪到属于自己的土坑旁,上半身依旧挺得直直的。
方语下意识摸了一把别在腰间的枪套,季曼笙按住她的腿,“别。”
“我们救不了所有人,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”
嘭嘭几声枪响,窗外景色变成了一群因受惊而起飞盘旋的乌鸦,学生们已经活在了上一幕的车窗外。
“想想你在老家种着地,等着老婆回来,结果运回的只有一盒骨灰和一个‘烈士家属’的袖套。”
季曼笙语气轻松得像在说什么好笑的事,方语却还没从刚才的情景中缓回神,等她再抬头,车子已经停到了城门口。
前方战事吃紧,守城门的活儿落到了警察厅头上,一名巡警弯腰叩了叩车窗,季曼笙摇下窗子,
“是我。”
巡警抬抬帽檐,低声道,“曼姐,老文在梧桐路口等您。”
车窗重新摇上,巡警举起一只手,示意同伴放行。
瞥见方语诧异的眼神,季曼笙略显得意,摘掉帽子扇了几下风,才解释道:“娘以前可是巡捕房的探长。”
好像是听说过这么一回事,怪不得……前面打着仗,后方却是畅通无阻。
如果不出意外,把信交给老文这次任务就算完了。
意外发生了。
车子开进城不久,一名新上任的巡警不认识谢家的车牌,拍着车盖儿将她们的车拦了下来。
他原是个流氓,警察厅缺人,无论地痞流氓,只要应聘统统上任,此等便宜,不捡白不捡。
上任后最要紧的事嘛,当然是搜刮油水。
“停车!老子叫你停车听到没!”
季曼笙环顾四周,确认周围没有其他行人后,将车停了下来。
“长官,什么事吗?”
“你的车违反了法规,罚款。”
车窗伸进来一只沾满酒气的白手套,季曼笙顺着手套向上望去,只见一顶戴歪了的警察帽,笑道:“哪条法规?”
“让你交你就交!哪来那么多屁话!”
“那……长官你靠近点。”
“什么?”警察将脑袋探进车窗。
季曼笙佯装拿钱,一手伸进操纵杆后方的阴影里摸索,一边朝方语丢了个眼色,方语会神,趁着警察盯季曼笙的功夫,迅速抽出手枪抵到警察脑门上。
“哎……”
车门猛地一顶,警察吃痛捂腿,另只手被擒起,一圈手铐利索地铐到了腕上,他刚要挣扎,两只手已经给人扭了一圈,手铐完整地铐住了两只腕子,
“阿语!”
方语连忙下车帮着季曼笙一起将警察塞进后备箱,同时捆住了那两条乱动的腿。
两人气喘吁吁坐回前座,方语比划道:[现在怎么办?]
“计划有变,先解决他。”
“喂!放老子出去!你们是什么人!信不信老子搞死你们!”后备箱里传来警察的谩骂与撞击箱盖的声响,方语爬到后座,给那张嘴封上一张胶布。
不知怎的,她总看这张脸有些眼熟。
车子绕到一条偏僻小巷,季曼笙打开后备箱。
后备箱里的家伙已经停止了挣扎,裤裆印出几块湿淋淋的形状。
“阿语,把他弄下车。”
方语去抱他,他抖得厉害,帽子抖落到后备箱里,脚一接触地面就软了,一个撑不住,直接瘫到了地上。
刀刃抵到咽喉处,季曼笙正欲动手,突然刀锋一转,将刀把递给了方语,
“你来。”
方语犹豫着接过刀。
“唔唔!唔唔唔!”警察像一条青虫,在地上疯狂蠕动。
方语蹲下替他撕开胶布,警察猛喘了几口气,大吼道:“方语!是我啊!王成刚!”
王……她想起来了,过去在村里,就是以王成刚为首的小流氓们经常欺负她。
“你们认识?”季曼笙靠近了一步,和方语一起蹲下。
方语点头。
“方语!我们同乡一场,以前我对不住你!我给你磕头!我给你磕头成吗?别杀我!求你别杀我!”
“他对不住你?”季曼笙捏住方语的手腕,把刀重新抵上警察的脖子,“那不是更该死?”
刃尖抵着血肉的感觉很微妙,她能感受到血在皮下流淌的动静,不禁泛上一股恶心。
“他不死,我们就会死。”
但是,能放他走吗?
她不能害死季曼笙。
刃尖浅扎进皮肉,鲜色的血从脖子上流了出来,手腕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,再往前深的时候,方语猛一抽手,松开了刀。
警察抓住这个机会并起双腿全力踹向她,方语捂着肚子跪倒,季曼笙及时捡回小刀。
寒光一闪。
“啊……咔咔……”是血液呛进喉管的声音。
再想说什么,也晚了。
警察大张开嘴,在方语面前死去了。
方语愕然地看着季曼笙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处理尸体。
扒光衣服、收起配枪、将尸体的脸划得面目全非。
“我就说你帮不上忙罢。”坐回车厢,季曼笙掏出手帕细细擦手上的污血。
方语垂下头。
她不怪季曼笙心狠,她怪自己差点把两人害死。
[对不起。]
“没事儿,我早知道的。”
车子启动了,方语扣着门把手,掉下几滴眼泪。
“所以不要怪表姐啦,只有那样,才能活很久、很久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梧桐路口站着一位戴平顶黑帽的男子。
季曼笙把沉知墨写的信交到他手上,又嘱咐了几句什么,男子连连点头,临要走了,男子从怀里抽出一枚信封递给季曼笙。
“曼姐,还有一封沉小姐的信。”
“哪儿来的?”
“有点远了,阿美丽肯。”
“知道了,你赶紧走罢。”
季曼笙坐回驾驶座拆开信封,方语听到了最后那几句,但侧过脑袋看向了另一边,不让自己去好奇信的内容。
“诶,你认识这个人吗?”
臂肘被顶了顶,方语转回脑袋。
“周筠。”
她接过信纸。
这是一封散发着海水的潮气,远渡重洋的求救信。
方语将信反复看了两遍,信中字里行间充斥着卑微的乞讨和对自己愚蠢决定的懊悔。
唯独没有,王雪梅三个字。
车子行驶到主干道上,洋场夜未眠,灯箱投出的光照得信纸一会变成红色,一会变成绿色,这场景与千里之外的家乡可谓毫不相干,窗外却吹过了相似的风。
很像埋葬王寡妇那天晚上吹过的风。
方语打开车窗,信纸碎成片片雪花,飘飘洒向街道。
这或许是她这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坏事。
狂风、暴雨、夜。
风卷着大雨扑面而来,一截细长的黑影躬着身子,进一步,退半步,踉跄地行走在铁路上。
手提电筒的光越来越近,晃晃映到雨幕里,为了躲避这只光的眼睛,黑影惊恐地趴到了地上,变为匍匐前进。
铁轨下的枕木散发出腐臭的气息,这里每根木头下面都埋葬着一位中国劳工的尸体,这是几十年前就经历过一次的教训,她怎么还会上当?
雨靴踩过碎石子,发出吱吱喳喳的声响,光落到手边,她停止了呼吸。
背心被雨靴踩出一个洞,靴底的碎石嵌进了肉里。
“找到你了,死猪仔。”
她先是感到疼痛,然后是愤怒,无止尽的愤怒,“你也是中国人!做这种事不怕遭报应吗!”
就是这个人,就是这个人……跟她说这里遍地都是机遇,面包多到拿来铺路,打开水龙头流的是牛奶,还慷慨地替她支付了60美元的船票。
即使睡在甲板底下经历了80天的颠簸,期间享受着和牲畜齐平的待遇,她也没有怀疑过这个人。
“报应?”衣领被提起,眼窝挨了一记重锤,一下、两下……她终于受不了了,滑下去抱住那只雨靴。
“求求你……求求你放了我……”
没有用。
那人揪住她的后衣领,将她往回拖,脚后跟踢踢踏踏击打着枕木,她几乎就要万念俱灰了。
是啊,求饶有用的话何必逃跑?
显然需要,更直观的好处。
父母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,还有谁能帮她?
一张脸闪过脑海,她惊叫起来,“我想起来了!我想起来了!”
“鬼叫唤什么?”
“你知道奉安的谢晋谢元帅吗?我有……”她捋捋乱抖的舌头,吞下一口雨水,“我有个姐姐,嫁给了谢元帅的女儿,只要你让我写封信!只要你让我写封信给她!她一定会帮我!你要多钱都行!”
雨靴在地面敲了几下,磕掉几颗石子,良久,头顶传来计算完毕的声音,“两千。”
“可以!可以!”
“信你一次,要收不到钱,你知道下场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树林一片片略过车窗,路边渐渐出现零星行人,挂着谢家的车牌,一路的小关卡畅通无阻,但城门那关……
方语将手伸出车窗,期望风能吹散紧张的汗水。
这是她第一次跟季曼笙出任务,今天的任务很简单。
送信。
如果她能干一些,压根用不着季曼笙顶着一张通缉令上的脸招摇过市,每次她想要帮她,季曼笙总会说,还不到时候,或者,你心太软,做不成事。
方语收回手,捏住膝盖,显出几分闷闷不乐之色。
“怎么?还在跟表姐闹别扭?”
摇头。
“表姐是毛病多了点,但有一点好……”
她向来很会断句,吊人胃口,方语忍不住偏了点脑袋,季曼笙借这机会瞟了一眼后视镜,接着说道:“就是自私。”
[自私有什么好?]
沉知墨的自私可害苦了她。
“我昨儿问表姐,如果鬼子拿枪逼她,让她交代事情,她会不会说,你猜怎么着?”
[她会。]
“对了,她会,在这年头是最聪明的选择,要死死一个,免得全家跟着遭殃。”
[我还是不懂。]
“那么你希望表姐在老家踏实跟你过日子吗?”
不……如果她渴求的是一位踏实敦厚的妻子,大可以在村里挑拣一位门当户对的,她喜欢沉知墨,一开始就是因为那一抹,不同。
追求新鲜事物是人的本能,她愿意供沉知墨念书,或许也是将自己对新世界的渴望投射到了沉知墨身上。
季曼笙换了只手握方向盘,朝窗外一抬下巴,“那就是不自私的人的下场。”
道路旁,几位身着长衫的学生被士兵推搡着前行,他们失去了昨日游行时的威风,面如枯槁,跪到属于自己的土坑旁,上半身依旧挺得直直的。
方语下意识摸了一把别在腰间的枪套,季曼笙按住她的腿,“别。”
“我们救不了所有人,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”
嘭嘭几声枪响,窗外景色变成了一群因受惊而起飞盘旋的乌鸦,学生们已经活在了上一幕的车窗外。
“想想你在老家种着地,等着老婆回来,结果运回的只有一盒骨灰和一个‘烈士家属’的袖套。”
季曼笙语气轻松得像在说什么好笑的事,方语却还没从刚才的情景中缓回神,等她再抬头,车子已经停到了城门口。
前方战事吃紧,守城门的活儿落到了警察厅头上,一名巡警弯腰叩了叩车窗,季曼笙摇下窗子,
“是我。”
巡警抬抬帽檐,低声道,“曼姐,老文在梧桐路口等您。”
车窗重新摇上,巡警举起一只手,示意同伴放行。
瞥见方语诧异的眼神,季曼笙略显得意,摘掉帽子扇了几下风,才解释道:“娘以前可是巡捕房的探长。”
好像是听说过这么一回事,怪不得……前面打着仗,后方却是畅通无阻。
如果不出意外,把信交给老文这次任务就算完了。
意外发生了。
车子开进城不久,一名新上任的巡警不认识谢家的车牌,拍着车盖儿将她们的车拦了下来。
他原是个流氓,警察厅缺人,无论地痞流氓,只要应聘统统上任,此等便宜,不捡白不捡。
上任后最要紧的事嘛,当然是搜刮油水。
“停车!老子叫你停车听到没!”
季曼笙环顾四周,确认周围没有其他行人后,将车停了下来。
“长官,什么事吗?”
“你的车违反了法规,罚款。”
车窗伸进来一只沾满酒气的白手套,季曼笙顺着手套向上望去,只见一顶戴歪了的警察帽,笑道:“哪条法规?”
“让你交你就交!哪来那么多屁话!”
“那……长官你靠近点。”
“什么?”警察将脑袋探进车窗。
季曼笙佯装拿钱,一手伸进操纵杆后方的阴影里摸索,一边朝方语丢了个眼色,方语会神,趁着警察盯季曼笙的功夫,迅速抽出手枪抵到警察脑门上。
“哎……”
车门猛地一顶,警察吃痛捂腿,另只手被擒起,一圈手铐利索地铐到了腕上,他刚要挣扎,两只手已经给人扭了一圈,手铐完整地铐住了两只腕子,
“阿语!”
方语连忙下车帮着季曼笙一起将警察塞进后备箱,同时捆住了那两条乱动的腿。
两人气喘吁吁坐回前座,方语比划道:[现在怎么办?]
“计划有变,先解决他。”
“喂!放老子出去!你们是什么人!信不信老子搞死你们!”后备箱里传来警察的谩骂与撞击箱盖的声响,方语爬到后座,给那张嘴封上一张胶布。
不知怎的,她总看这张脸有些眼熟。
车子绕到一条偏僻小巷,季曼笙打开后备箱。
后备箱里的家伙已经停止了挣扎,裤裆印出几块湿淋淋的形状。
“阿语,把他弄下车。”
方语去抱他,他抖得厉害,帽子抖落到后备箱里,脚一接触地面就软了,一个撑不住,直接瘫到了地上。
刀刃抵到咽喉处,季曼笙正欲动手,突然刀锋一转,将刀把递给了方语,
“你来。”
方语犹豫着接过刀。
“唔唔!唔唔唔!”警察像一条青虫,在地上疯狂蠕动。
方语蹲下替他撕开胶布,警察猛喘了几口气,大吼道:“方语!是我啊!王成刚!”
王……她想起来了,过去在村里,就是以王成刚为首的小流氓们经常欺负她。
“你们认识?”季曼笙靠近了一步,和方语一起蹲下。
方语点头。
“方语!我们同乡一场,以前我对不住你!我给你磕头!我给你磕头成吗?别杀我!求你别杀我!”
“他对不住你?”季曼笙捏住方语的手腕,把刀重新抵上警察的脖子,“那不是更该死?”
刃尖抵着血肉的感觉很微妙,她能感受到血在皮下流淌的动静,不禁泛上一股恶心。
“他不死,我们就会死。”
但是,能放他走吗?
她不能害死季曼笙。
刃尖浅扎进皮肉,鲜色的血从脖子上流了出来,手腕上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,再往前深的时候,方语猛一抽手,松开了刀。
警察抓住这个机会并起双腿全力踹向她,方语捂着肚子跪倒,季曼笙及时捡回小刀。
寒光一闪。
“啊……咔咔……”是血液呛进喉管的声音。
再想说什么,也晚了。
警察大张开嘴,在方语面前死去了。
方语愕然地看着季曼笙用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处理尸体。
扒光衣服、收起配枪、将尸体的脸划得面目全非。
“我就说你帮不上忙罢。”坐回车厢,季曼笙掏出手帕细细擦手上的污血。
方语垂下头。
她不怪季曼笙心狠,她怪自己差点把两人害死。
[对不起。]
“没事儿,我早知道的。”
车子启动了,方语扣着门把手,掉下几滴眼泪。
“所以不要怪表姐啦,只有那样,才能活很久、很久。”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梧桐路口站着一位戴平顶黑帽的男子。
季曼笙把沉知墨写的信交到他手上,又嘱咐了几句什么,男子连连点头,临要走了,男子从怀里抽出一枚信封递给季曼笙。
“曼姐,还有一封沉小姐的信。”
“哪儿来的?”
“有点远了,阿美丽肯。”
“知道了,你赶紧走罢。”
季曼笙坐回驾驶座拆开信封,方语听到了最后那几句,但侧过脑袋看向了另一边,不让自己去好奇信的内容。
“诶,你认识这个人吗?”
臂肘被顶了顶,方语转回脑袋。
“周筠。”
她接过信纸。
这是一封散发着海水的潮气,远渡重洋的求救信。
方语将信反复看了两遍,信中字里行间充斥着卑微的乞讨和对自己愚蠢决定的懊悔。
唯独没有,王雪梅三个字。
车子行驶到主干道上,洋场夜未眠,灯箱投出的光照得信纸一会变成红色,一会变成绿色,这场景与千里之外的家乡可谓毫不相干,窗外却吹过了相似的风。
很像埋葬王寡妇那天晚上吹过的风。
方语打开车窗,信纸碎成片片雪花,飘飘洒向街道。
这或许是她这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坏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