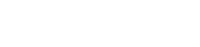岑冬青洗了热水澡,换上了睡衣——他家没有女士睡衣,找了一套他的,毛茸茸的,很大。
池以恒强调自己没穿过,但她莫名觉得衣服上有他的味道,很好闻。
袖子太长了,她卷了几圈才露出手,池以恒在外面敲门,说要给她送热牛奶。
黄鼠狼给鸡拜年,不安好心。
岑冬青倒要看看他又有什么新花样。
开了门,他端着热牛奶走进来,放在她跟前,要给她吹头发。
哎呦,还会给女生吹头发呢。
她没说什么,想看他露馅。
然后发现他并不会吹,很是生疏地摆弄她的头发,看上去很镇定,但其实手指在她发间穿来穿去的,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
岑冬青笑了。
好傻啊。
她等池以恒给她把头发吹完,他也洗过澡换了睡衣,头发看上去只是草草吹了一下,还有些湿漉漉的,一副打算和她睡觉的样子。
她眨着眼睛,眼睛里是狡黠的笑意。
“晚安。”
池以恒闷闷不乐地:“晚安。”
再次被驱逐出房间。
明明都跟他回家了。
“啪”地一声,灯灭了。
陷入一片黑暗。
池以恒抓住了她的胳膊:“别怕。”
我没怕!岑冬青被他吓了一跳:“停电了?”
池以恒“嗯”了一声,偷偷低头闻她头发上的香味。
她离得那么近,近到只要一伸手,便能抱个满怀。
他没忍住,伸出了手,把她搂进怀里,他心跳得好快。
岑冬青也心跳得好快,黑暗里,他是唯一的温度,很热很热地贴着她,她腿有些发软,好想睡他。
他的呼吸有些重,就在她耳边。
“我能亲你吗。”
真要命,怎么会有这种人。
明明高大有力,能把她按在怀里肆意妄为,可他却很有礼貌地询问她,能不能亲她。
岑冬青在他怀里仰起头,他以为她要挣扎,用力地把人搂得更紧。
好想——
他下面那根东西隔着衣服顶在她身上。
他是混蛋,他想强——
他被自己荒唐的念头撩得浑身发烫,耳朵热得像要熟了。
“就给我亲一下·······”
他可怜巴巴地问,“一下也不行吗。”
啧!
岑冬青想强吻他了!
她在黑暗里踮起脚,亲在他的下巴上。
好像火山喷发,炙热的岩浆滚过四肢百骸,池以恒本能地吻住了她,他脑子里一片空白,下意识地轻啄到舔舐,再到吮吸,舌头忍不住地闯进去,压着她的舌头,缠着她嘬吻。
岑冬青还是第一次接吻,初吻的威力叫她晕乎乎地软在池以恒怀里,发出令人脸红的呻吟。
喘不过气了。
她不知道怎么呼吸,被亲得满脸通红,等他放开时,像只缺氧的鱼在他怀里喘息。
紧接着池以恒又吻住了她,他把人压在床上,深深陷入柔软的被子里。
十指紧扣,亲了又亲。
他无疑是高大的,这样罩在她身上,好像一座小山,又像是什么远古巨兽,纤细的身子在他身下无力地挣扎。
也不是真的不愿意,只是她受不了这么猛烈的攻势,又慌张又想要,扭着身子想挣脱禁锢,有想要更多。
池以恒强调自己没穿过,但她莫名觉得衣服上有他的味道,很好闻。
袖子太长了,她卷了几圈才露出手,池以恒在外面敲门,说要给她送热牛奶。
黄鼠狼给鸡拜年,不安好心。
岑冬青倒要看看他又有什么新花样。
开了门,他端着热牛奶走进来,放在她跟前,要给她吹头发。
哎呦,还会给女生吹头发呢。
她没说什么,想看他露馅。
然后发现他并不会吹,很是生疏地摆弄她的头发,看上去很镇定,但其实手指在她发间穿来穿去的,不知道自己在忙什么。
岑冬青笑了。
好傻啊。
她等池以恒给她把头发吹完,他也洗过澡换了睡衣,头发看上去只是草草吹了一下,还有些湿漉漉的,一副打算和她睡觉的样子。
她眨着眼睛,眼睛里是狡黠的笑意。
“晚安。”
池以恒闷闷不乐地:“晚安。”
再次被驱逐出房间。
明明都跟他回家了。
“啪”地一声,灯灭了。
陷入一片黑暗。
池以恒抓住了她的胳膊:“别怕。”
我没怕!岑冬青被他吓了一跳:“停电了?”
池以恒“嗯”了一声,偷偷低头闻她头发上的香味。
她离得那么近,近到只要一伸手,便能抱个满怀。
他没忍住,伸出了手,把她搂进怀里,他心跳得好快。
岑冬青也心跳得好快,黑暗里,他是唯一的温度,很热很热地贴着她,她腿有些发软,好想睡他。
他的呼吸有些重,就在她耳边。
“我能亲你吗。”
真要命,怎么会有这种人。
明明高大有力,能把她按在怀里肆意妄为,可他却很有礼貌地询问她,能不能亲她。
岑冬青在他怀里仰起头,他以为她要挣扎,用力地把人搂得更紧。
好想——
他下面那根东西隔着衣服顶在她身上。
他是混蛋,他想强——
他被自己荒唐的念头撩得浑身发烫,耳朵热得像要熟了。
“就给我亲一下·······”
他可怜巴巴地问,“一下也不行吗。”
啧!
岑冬青想强吻他了!
她在黑暗里踮起脚,亲在他的下巴上。
好像火山喷发,炙热的岩浆滚过四肢百骸,池以恒本能地吻住了她,他脑子里一片空白,下意识地轻啄到舔舐,再到吮吸,舌头忍不住地闯进去,压着她的舌头,缠着她嘬吻。
岑冬青还是第一次接吻,初吻的威力叫她晕乎乎地软在池以恒怀里,发出令人脸红的呻吟。
喘不过气了。
她不知道怎么呼吸,被亲得满脸通红,等他放开时,像只缺氧的鱼在他怀里喘息。
紧接着池以恒又吻住了她,他把人压在床上,深深陷入柔软的被子里。
十指紧扣,亲了又亲。
他无疑是高大的,这样罩在她身上,好像一座小山,又像是什么远古巨兽,纤细的身子在他身下无力地挣扎。
也不是真的不愿意,只是她受不了这么猛烈的攻势,又慌张又想要,扭着身子想挣脱禁锢,有想要更多。